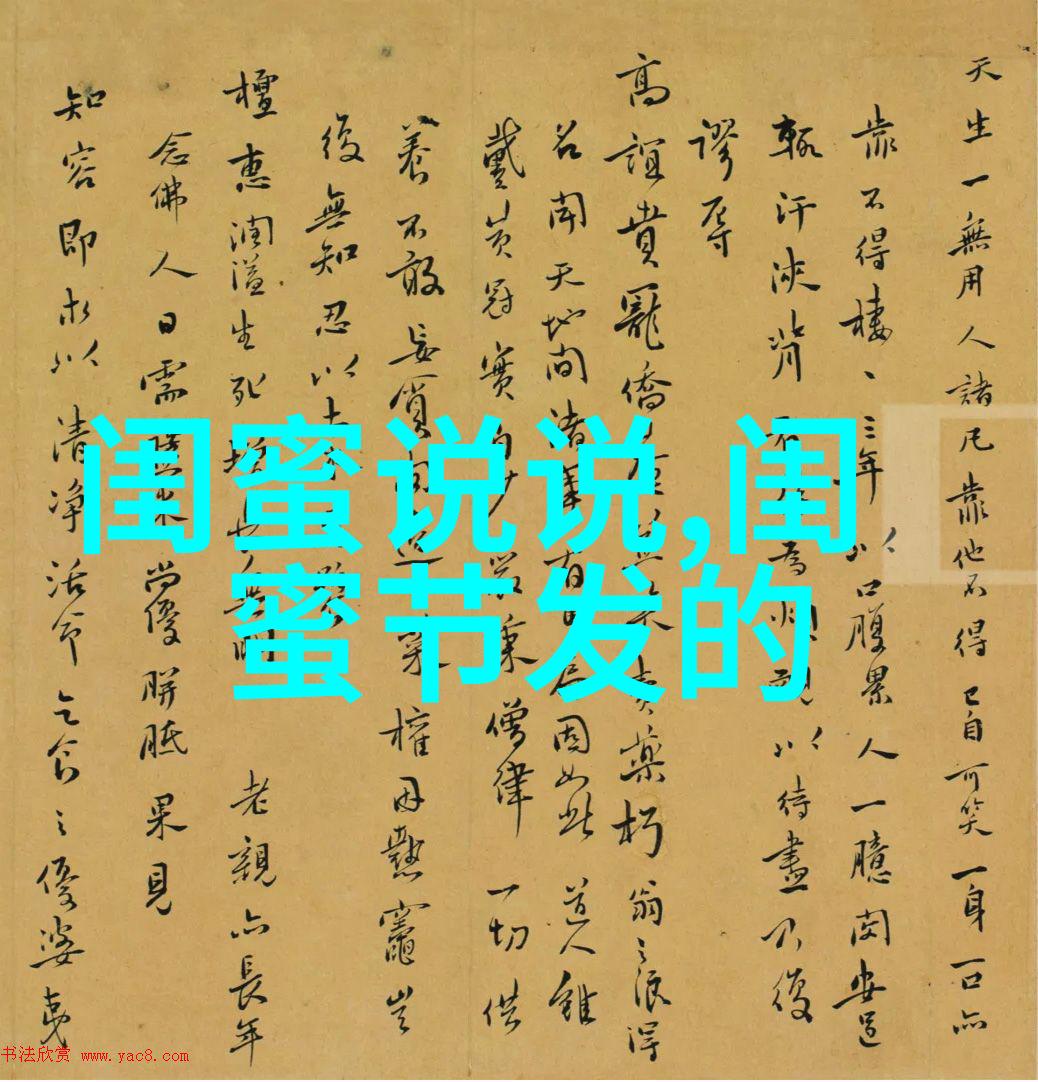
有人说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就是孩童的心
外面下着雪,我一个人安静地靠在窗边,凝看着外面的雪花。——题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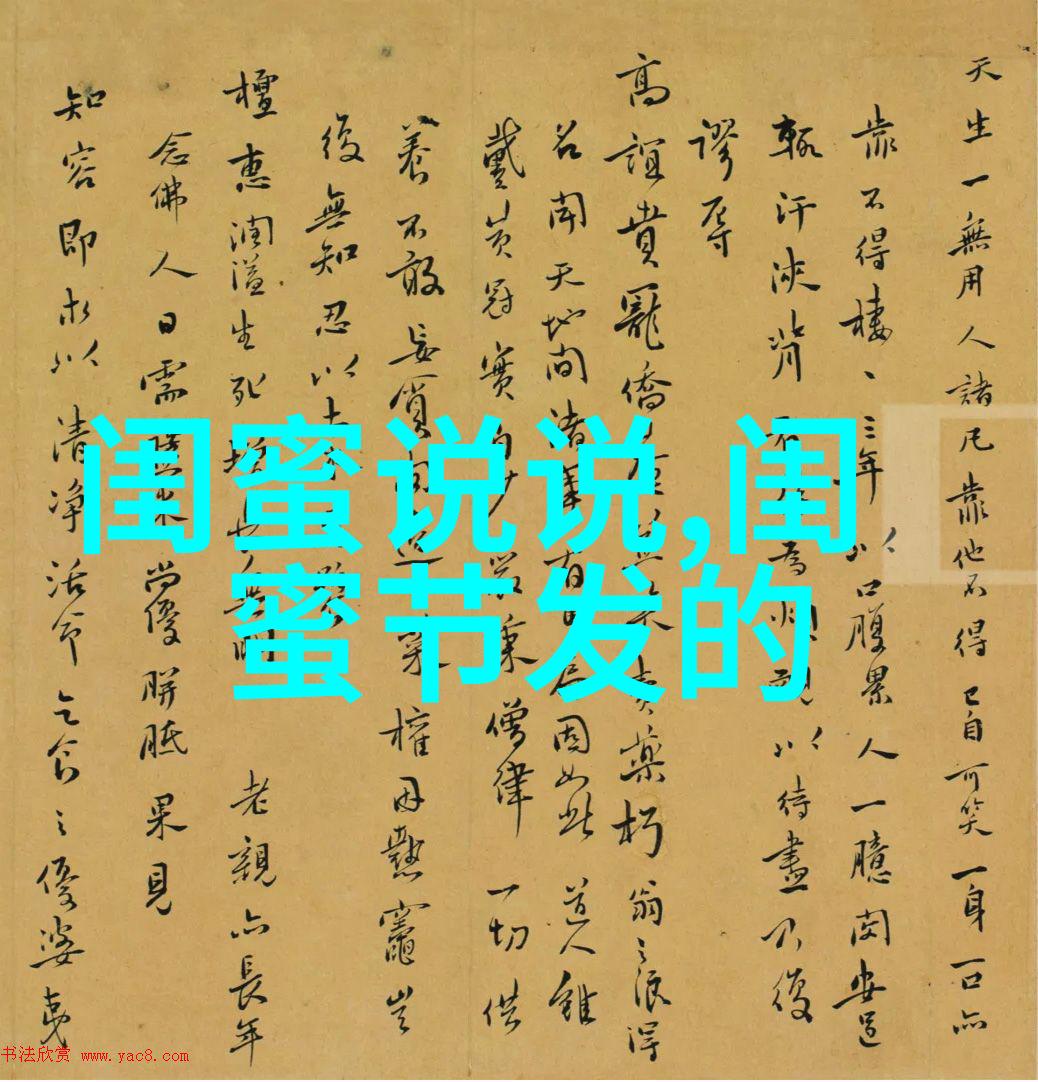
有人说,世界上最纯洁的东西就是孩童的心,可是,如今的世态已经不再是那样了,孔子奉行先做人,再做学问,而如今却反过来了,先学做文,再学做人,是故有很多衣冠楚楚的文化分子,其修养素质,谈吐做事反倒不如一个质朴的农民。孩童在这样的社会里,怎么会拥有一颗纯洁的心呢?炫耀衣物,攀比学业,等等。
其实,我倒是觉得最纯洁的是雪,如同现在我看着的飘雪一样,将整个黑夜都映的恍如白昼。往往美好的东西都能引发人们的愁绪,因为总怕它来得太愉悦,走时定然会心生留恋,不忍。雪花一片一片地飘下,我偶然会伸出手接住一朵,若是不融化,我便想将它送给一个人,或许是温度太低的缘故吧,它在我的手里待了足足一分钟,也没有融化,或许是让我想起那个我要送她雪花的人,可是我想不到哪里有那么个人。

最后,雪花给我的时间已经够多了,我实在也想不到将它送给谁了,它便尽力地挨到最长的时间里,无奈地融化了。我看着手里的水珠,呆了,方才还是一朵六角雪花,让我想起要将它送给一个人,让我思索我的思念,可现在却消失不见了,只剩下一滴看惯了的水珠,是否我的思念住得太远,是否一切美好都会消失得这么迅疾?是否我注定了探索不到那个人的存在?
猛然想起一句人们传颂已久的爱情格言,如果我每想你一次,天空就飘落一粒沙,那么我对你的思念如同撒哈拉。这场大雪是不是也在飘落着某人的相思?只是这相思永远住在北坡上,明明就在坡上,却从来不向阳。

漠漠复纷纷,东风散玉尘,白居易是这样形容雪的,玉尘,我轻轻地念着,只觉得这样的称谓再恰当不过了。在岁月的波澜不惊里,它每逢年味将至的时候便会施然袭来,让那些期盼团圆的人成了风雪夜归人。我虽然是静默地看着,可心里却并非没有杂念,雪花是温柔的,夜色也是温柔的,两重温柔交缠在一起,我实在不愿意辜负。于是我便披上披风,穿着母亲手做的棉鞋,静静地走进了雪海里。
临迈出门的那一脚,我有些犹豫,或许是有些寒冷吧?不是的,难道是怕湿了鞋?也不是的,湿了鞋我可以晾干它,母亲的心总是湿不了的。突然我想到了,我之所以会犹豫不决地不敢迈出这一步,是怕走进了雪海里,再也走不出红尘了。

咯吱咯吱的声音,伴随着我的脚步,在雪花静静飘落的夜晚荡漾开来。我终究还是出来了,穿着母亲手做的棉鞋,安安地一步一步踏了出来。我走了片刻,将充满暖意的房屋远远抛在了身后,抬头看着浩瀚苍穹,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。雪花小若蝇腹,却能改变大地的初装,我空有一双健全的手,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。我转头看了看身后的光亮,我从温暖处走来,只为迎接一场寒冷。
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决然地走出来,难道仅仅是不愿意辜负这夜景吗?还是我修行不够,无法抵抗红尘的,想一吻繁华。我思索良久,却得不到答案,安静的夜色有了些纷扰,我的心也被扯进了纷扰里。我不是原路返回的人,便没有管身后的脚印是否错落有致,是否已被掩埋,毅然向前行去。

我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?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种坚持?我只是明白身后的温暖不是我的家,即便会沐浴严寒,我也不惧不怕,因为我知道:家就在行者的脚下。
临近华人春节之际,独自一人远在他乡,总是不免看着美景思索乡愁,这红尘呀,你总是将我和母亲隔在两头,温暖在这头,寒冷在那头。
每每回乡前,总是迫不及待。
我从城里令人窒息的雾霾里,我在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中“冲回”老家了。一个如梦如幻,山清水秀的小山村。
我大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我高声地和乡亲打着招呼,我脚下虎虎生风,我意气风发,我从人到中年回到青年。
见到母亲,我像个女人,热泪盈眶的激动里,是喋喋不休地说话再说话,我压抑得太久了,我不吐不快呀!
阳光明媚,我在老家的沿渠上漫步,一弯清清的溪水缓缓地流动,四围群山环绕,鸟语花香。那株株青松傲然挺立,枝繁叶茂,清风徐徐,轻轻摇摆,似在欢迎我的到来。我沉醉其中,我浑然忘我。
晚上,月光如水,潺潺的小河,静静的田野,山上那一片片高低各异,摇曳多姿的树丛,我往往一边欣赏,一边听着随带的音乐,绝对地放松,绝对地心旷神怡。
碰到邻里吃饭,硬要把我拉到桌上,一脸的真诚热情,不好拒绝,便欣然就坐了,那山野菜的清香,那玉米粥的香甜,让我口齿留香,口福大饱。
老年秧歌队锣鼓喧天,我的母亲合着节奏,喜笑颜开,我依稀看到艰辛岁月里母亲那愁惨的面容,对比今昔,让人感慨万千。
老家的集镇,熙熙攘攘,一声吆喝,一阵期待,更是一种自得其乐。搞搞价钱,寒寒喧喧,成交了,还成了朋友。
有人不幸患了癌症,乡人都很难过,忆起此人的好,无不难过抹下眼泪,纷纷前去探望,陪病人坐到深夜。东家鱼,西家虾,病人明天都有好吃的;去世了,本是老人儿童世界的乡村,会突地出现一批生龙活虎的,在外打工匆匆赶回的男子,抬棺材上山埋葬,那种艰难险阻,那种前赴后继,奋力协作,让人震撼!
我在年老时,一定要回到故乡。








